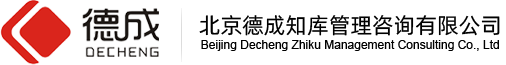当前位置:走进德成 > 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被误解的陶渊明

被误解的陶渊明
按语:对历史的文化反思似已沉寂,数年前有个余秋雨。《被误解的陶渊明》却给你一种全新的冲击和感动,一种着眼明天而扯动前天的疼痛。他,不是余秋雨,他是龚益鸣。
陶渊明,因敬畏,我不敢碰触这个名字。
还是在读中学的年代,我就曾被老师教训:不要像陶渊明那样消极厌世,有不健康的出世情结。那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出世”,也不知道谁是陶渊明。于是,出于好奇,便提早走近了陶渊明。
历史似乎还停留在那个年代。今天我们随处可听见众多党政干部甚至专家学者,他们仍然把“消极颓废”、“不思进取”、“自甘堕落”、“没有事业心”种种罪名安到陶渊明的头上,用来指责他们认为落后的人。
天理良心,陶渊明在最应该被仿效、被推崇的时代却遭受到最不应该的指控,这让我们领教了无知的偏见是一股何其强大的力量。于是,我不能因敬畏,而不敢再次走近陶渊明。
一千四百多年前,第一个全面走近陶渊明的人叫萧统。他是南梁小朝廷的储君(昭明太子),那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中国历史上有些很奇怪的方面,越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文化往往越兴盛。譬如南唐、南宋和南明。东晋南朝也是这样。那时,北方被少数民族的铁蹄蹂躏一空,世族大姓纷纷南逃,他们是真正不思进取的一群,除了成天在“江亭对泣”,便是在声色犬马中寻找麻醉。于是得过且过的颓废心态与北方带来的魏晋玄风相结合,便迅速形成了东晋乃至席卷其后宋、齐、梁、陈各代专务形式美的没落的文风。人们做诗一味追求用典,专在词藻上雕琢,务求富丽工整,至于思想内容却全然不顾。
那个养尊处优的昭明太子也是个爱诗写诗之人,但他显然已开始厌倦潮流。一天,他接触到当时著名批评家钟嵘所著的《诗品》,他翻过“上品”还是那些面孔,于是又信手翻到“中品”,便想一丢了之。但突然他的眼睛定格了,他看见了这样的文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不啻于冬天的一记响雷,震散了弥漫的阴霾,他目瞪口呆。当他再次定神阅读时,一座美学的高峰、思想的高峰和人格的高峰便在眼底渐次展开。他记住了那个名字:陶渊明!而那时,陶渊明离开这个世界已快百年了……
我们得感谢萧统,这个只活到三十一岁的储君。如果说他短暂的一生做过什么有意义事情的话,那就是他编写了第一部《陶渊明集》,是他出自对陶渊明“文”与“德”的高度崇拜而开始的搜集陶渊明的自觉行动。于是,靖节先生142篇诗文便慢慢汇聚成一条平静而又激越、清澈而又幽深的大河穿越时空流传至今。
看看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吧。
他说读了陶诗:“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陶诗是真正的“独起众类”,“莫与之京”,简直是“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萧统似乎就是比今天的青年人智慧,他一下子就发掘出了陶诗的精髓。瞧瞧:那是让人鼓起担当责任、直面人生勇气的风帆;是让人去贪鄙、求廉洁的良药;是让懦夫可以立志,愚劣可至仁义的标尺;是勇敢的探索者以正风俗为己任而挥洒的直薄云天的阳光!这里,哪里有丝毫的“出世”、“颓废”可言?

感动过历史的东西不一定能感动现代,但感动过灵魂的思想注定会永世长存。
陶渊明能感动中国千年,首先是他的自然美。很多人不喜欢陶诗,认为它过于直白不事雕琢,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这不就是说话吗?它哪有李白的汪洋姿肆,杜甫的含蓄浑厚过瘾?殊不知,这正是陶渊明的刻意所为。他要挽狂澜于既倒,矫正那颓废的文风,而他的宗旨和武器就是“抱朴归真”,直诉自然之美。于是便有了“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白描;有了“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视野;有了“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的静思……而这一切在那个时代是一股真正的淳风,它一扫专以饮宴和舞女入诗,围绕着没落士大夫狭窄心胸作无病呻吟的积习。没有陶渊明,先秦“风骚”的讴歌自然不可能进入诗词圣殿的主流,不可能有唐诗宋词的壮阔大河,甚至不可能有朱熹“格物致知”的滥觞。因为正是陶渊明“物我一体”的咏呤以后世的哲学以莫大的启迪。
人的审美意趣和水平是有层次的。耐人寻味的是,大唐的诗坛巨擘几乎无人不受陶渊明的影响,特别是白居易几乎完全师法陶潜,“二李”、“二杜”和元、白的那些隽永的吟唱都可从陶诗中找到脱化而来的踪影。但他们对陶渊明却褒贬不一。大唐的空前统一和宽松的环境给了士人广阔的发展天地,他们没有陶渊明那样窘迫的生存环境,也不屑于作“以物咏怀”的无谓抗争。只是到了有宋一代,人们才从自我渲泄的陶醉中完全走出,领略到了广阔的自然之美和天人合一的无上境界。于是陶渊明在宋人那里成了神,陶诗登上了超过李、杜,可与“风骚”比肩的巅峰之作。陆游就无限崇拜地倾诉:“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千戴无斯人,吾将谁与归?”
是的,宋人的审美意趣是高超的,从形式美到自然美是一大进步,从雕琢的美到返朴归真的美是一个超越。实在说,没有陶渊明,我们今天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生态的共进便失去了一个理性的座标和依归。而这一切,又正是陶渊明在那个遥远的黑暗时代作革命性的抗争而早早地树立起来的。他何尚“消极”了半点?
我自己并不经常读陶诗,甚至在消遣的阅读时也会跳过它直奔唐宋和曹雪芹,可是陶渊明是真正令我敬畏的伟大诗人,甚至是唯一的诗人,这就是他的人格的魅力。
人格的魅力恰恰来自他那被人千古诟病的“退隐”!
陶渊明因退隐而背上消极避世的批评由来已久。但不管历朝历代的少数文人和官僚怎样批评他,唯独当代中国的社会良知不能指责他,因为那是向黑暗的抗争,是陶渊明正式“积极出世”的开始,是一系列创造的起点,是民族伟大人格的诞生。
陶渊明的退隐实际包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退隐?退到了哪里?退了又怎么样?这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包含着给人悲怆式的启迪。
陶渊明退隐的原因:这只要一句话便可回答:他感到在官场无所作为和志愿的即将落空。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朝,是门阀等级森严的社会。不是豪门大族,不可能晋升到高级官僚的行列。而他只是一个低级士族,有人说他的曾祖是“晋世宰辅”陶侃,纯属子虚乌有。陶渊明素有“大济苍生”的志愿,所谓“猛志逸四海,骞然思远翥”,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活画出一个青年俊才急于报效天下的形象。于是,为了施展抱负,同时也为了“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生活,他29岁时终于出仕了,他奔走在浔阳至建康的各条道路上,他先后断断续续在桓玄、在刘裕、刘敬宜的衙门里做过“祭酒”、“参军”一类小官。这几派军阀势力那时都在铆足劲儿为夺取残存的司马氏政权而残酷互斗。于是,像鲁迅说的那样: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他面对“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的黑暗政局,连悲伤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力量去弥补?于是,他在最后一任彭泽县令任上呆了八十多天,便毅然决然地退出了官场,不论其后官府几次征召,我们的靖节先生却是志坚如钢,一去不回头!
他退到了哪里?他不象孙登一类隐士,退到山林,与鸟兽为伍;也没有退回豪门深宅,沉于纸醉金迷;更没有遁于空门,尽管他的好友慧远和尚就在庐山。他退归了哪里?退归了田园,当一个读书耕地的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士族农民”!于是,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断言:他不是退隐,而是“转业”!
他退得如何?旧时的隐士可分四类:以隐避祸(如竹林七贤);以隐待时(如贾谊、诸葛亮);以隐求名(如殷浩,越隐官做得越大);以隐泄怨(如介子推负母入山)。可是,陶渊明与此全然不同,他是真正的退出。退得自觉自愿,心平气和,不带半点怨恨,不参杂一丝回头的奢望。因为他要去从事“颇示已志”的事业,不愿尸位素餐,所以他退得铁一样的笃定和淡定!他不象杜甫那样苦苦挣扎,没有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彷徨,也没有曹雪芹辛酸热泪的呐喊,那是因为他对自我选择的道路及其“短褐穿结”的窘迫生活有安然自得的心态。他微笑着看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这就是陶渊明。因此,他可以义无反顾,“戴欣戴奔”地永别官场!
这个“三退”(退得坚决、退得淡定和以退为进),足以让陶渊明光耀千秋。朱熹就说过:“晋宋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清淡,那边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依我看,何止晋宋,扒拉一下古今中国,可有第二个陶渊明?当然没有。因为没有他真正视名利如粪土的心怀,没有他那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今天我们如何认识这种退出?这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民族是需要一个封建军阀不起眼的帮凶,还是需要一个光耀千秋的陶渊明?
中国历代的知识份子都有一个致命的认识误区;似乎认为自己的价值和抱负只有出仕才能体现,才有意义。因此,只有当官才是最高和唯一的社会承认。否则,就叫“出世”,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根本不想去思考,一切专制的政权及其官僚体制,实质上都是为着一家一姓一派争夺和巩固自身对人民的压迫而存在的。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反社会、阻碍文明进步的。对专制政权下官僚的主要功能,只有陶渊明一人认识清楚了,他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矫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巧取豪夺。可怜的是知识份子自身没有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既没有能力也根本不想自立,必须也只能依附于统治阶级,从人民那里分一杯羹,这就是所谓的“皮毛论”。他们不甘心做“毛”,乐于自我欺骗,所以认为出仕是在报效社会。如今,电光一闪,有个陶渊明站出来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们恼羞成怒了,岂能不把所有的脏水泼向这个叛逆者?
陶渊明是伟大的。他出仕的经历使他完全认清了这一点:除了挣个活命钱外,在官场整个自我及其理想都会丢失。他痛感“道丧向千戴,人人惜其情”,“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他向往着黄帝和虞舜那上古平等的太平世界,而自己“性刚才拙”,在官场“冰炭满怀抱”,“如果“缠绵”下去,必负“素志”,因此不如退出。那样,即使生计无着,还可以从事诗文的创作和改造社会的研究。这是一种何其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责任心啊!
陶渊明觉醒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全世界还处在漫长的看不见尽头的昏睡中。
是的,直到一千五百年后,才有个叫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法国人出来总结了这一切。那就是萨特关于人的“自在与自为”的理论。我们没有必要对存在主义哲学中“人的实在性”展开争论,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在一个开放平等的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存在形式可以自我设计和追求,而不必依赖或附庸于某个权力中心。“自在”——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是自我根据主客观条件设定的;“自为”——个体根据自我设计的目标为之自觉地奋斗。显然,这种“自在”与“自为”必须依赖公民社会的自由择业制度,更依赖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完成。可是陶渊明却“迫不及待”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就撞入了这一“禁区”,这既是他被千古误解,又是他被千古仰视的原因所在。
遗憾的是,陶渊明能够自为的空间和可选择的余地实在是太狭小了。
在一个专制、传统而破败的农业社会,穷苦的知识份子不入仕,就只有两条路可走:“犁耕”和“笔耕”!陶渊明贪心太大,他两者都抓了过来,两者同时扛在肩上。“笔耕”:他写了142篇诗文,给民族文化垒筑了一座突兀的高峰;“犁耕”:他“开荒南野际,守独归田园”,“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今人说他只是走向底层,接近农民,甚至说他是收租的庶族地主。这大大降低了陶渊明“转业”意义,也完全不是事实。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新农民”!这样一种抉择,别说在封建士族中绝无仅有,今天稍有门路的知识份子(包括笔者)也绝难望其项背!

陶渊明自为的代价是沉重的,也就是说,他经济学上付出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太高昂了,他几乎就是傻帽一个!他原来当官,接济家用,尚可“有酒盈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可是,自断经济来源,他便把自己及其家人抛入了一个更加窘迫,更不确定的险境。他的自为之路,使他成为一个失败的官僚、失败的丈夫(两任妻子先后死亡)、失败的父亲(几个儿子均不“成器”),甚至是一个失败的男人。他明知会这样,于是便更努力地犁耕和笔耕。但不善务农的他收获的只是“草长豆苗稀”,而沉重的赋税、火灾、虫灾、洪灾并不对他特别宽容,原来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屋”可能已所剩无几。他终于弄到“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的境地。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最后的一幕。
公元426年5月,江州刺史檀道济听说陶渊明如此苦寒,特来访问并送上肉、米,被陶拒收,这是他归田后多年少有的来访者之一。远处是庐山慧远和尚的佛堂,那钟声的感召被他象蛛丝一样轻轻拂去。他点亮了昏暗的豆油灯,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认真地写着蝇头小楷。他正在抄写一份他的旧稿,借着昏暗的灯光,那纸上赫然几个大字:《桃花源记》……九月,他卷缩在床上,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旧病的折磨。他想喝口水,却无人答应。他无奈地望着草屋顶上那个破洞展示的夜空,夜空象他的心一样迷茫空旷。于是,他的眼睛不再转动也不愿转动了。那时,南北分治的山河一片紊乱,而在紊乱之中仿佛有一刻死一样的静默,为谁默立?不知道。因为一个民族刚刚用她铅灰色的冷漠窒死了一个默默无闻但却是她最优秀的儿子,尽管那种静默不带有一丝忏悔,也从不忏悔……
三百年后,《桃花源记》被群起仿效,形成蔚为壮观的散记文学;
一千三百年后,《桃花源记》受到世界性的关注和研究;
一千五百年后,人们认定:《桃花源记》是最早的社会主义文献,尽管它带有空想和农业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它仍然是一篇伟大的文献……
- 上一个:跟着共产党学管理之三:使命驱动的组织 2019-03-22
- 下一个:【行而思】回归城市思维 2019-03-22
德成动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7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6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5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夸父逐日
- — 市政府国资委召开国资国企转型发展及“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