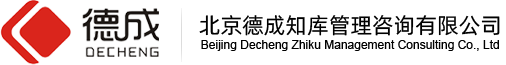当前位置:走进德成 > 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行而思】回归城市思维

【行而思】回归城市思维
——1956哈佛城市设计会议
与1950-1970年代波士顿城市更新的启示
图、文 / 胡晓玲
胡晓玲
武汉市规划研究院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注册城乡规划师,南京大学博士,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
近期读到一本介绍1956年哈佛城市设计会议(以下简称哈佛会议)的论文集《城市设计》,联系到案头时常研读的《建设新波士顿:1950-1970旧城更新中的政治》(以下简称建设新波士顿),顿感哈佛会议与波士顿旧改之间的必然联系。而当前武汉市及中国其他城市在旧城更新、城市活化、文化传承与创新所面临的的状况与当时的波士顿具有极其相似之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通过对哈佛城市设计会议议题、背景及主要贡献的介绍,与同时期波士顿所面临的城市更新困境和出路、采取方法进行比对,总结高校与城市的相互作用,与中国现阶段发展转型以及城市更新面临的问题相比较,总结可借鉴的经验包括回归城市、公共参与多方合作、大学与城市的关系等等,总括为“回归城市思维”。
1956哈佛城市设计会议与建设新波士顿运动
(Building a New Boston)
1956年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召开了一场关于城市设计的重要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的两个议题分别是中心区和社区的意义,参会者全是一些有声望的建筑师或规划师,如被称为城市设计之父、时任哈佛设计研究生院院长的何塞·路易·塞特,建筑学教授罗伯特·格迪斯,费城规划师爱德蒙·培根,也有刘易斯·芒福德和简·雅各布斯以及MIT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亚当斯、哈佛法学院教授查尔斯·哈尔等这样的城市学家、社会学者,还有匹兹堡市长大卫·劳伦斯,政策研究者、作家查尔斯·爱布拉莫斯等。
会议挑战以往的城市设计仅仅只是处理城市的物质形态,体现的是“城市的瓦解和建筑、景观、社区居民、业主等等各方面各自为政”,转而推崇综合性的“城市思维”“城市胸襟”和城市设计中各方面专家的合作。会议对城市的再认识为城市设计厘清了“思维的框架”,注入了新的源动力。并提出城市设计是一种“思考方式”,是“大尺度建筑”,是“场所营造的艺术”。
哈佛会议引发了城市设计是关于城市建筑空间的设计还是关于城市的设计的长期激烈的讨论,被称为第一届城市设计大会,是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开端和重要基础。哈佛大学也成为全球城市设计学术领域的制高点,始终引领着城市设计学科的发展。
1950年代初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美国城市来说更是如此。1949年是美国总统换届年,波士顿也于1949年由曾任前政府书记官的约翰·B·海恩斯接替在任达40年的前市长,在任10年,正是波士顿革新旧城市“建设新波士顿”的关键时期。波士顿是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心城市,在此爆发了美国独立战争,是马萨诸塞州首府,被公认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有文化和活力的城市。这不仅是因为它有哈佛、MIT这样的名校,更是因为它有丰富的历史遗存、众多的美术馆、完好的宜人的中心区。就像《建设新波士顿》一书中所描述的——古色古香,蜿蜒的街道,高耸的教堂,一连串的剧院,几百年时尚的酒店和餐厅、商铺以及学校,非常具有活力,是一个让波士顿人以及游客都流连忘返的地方。
相比芝加哥、纽约的辉煌发展,1890年代是波士顿比较沉寂的年代。1907年波士顿建筑师协会提出一系列“建设新波士顿”的建议,包括一系列物质空间、公共设施、林荫道等规划。1909年编制的“波士顿1915计划”是一份有关物质和社会改良的综合规划,强调改善公共教育、公共健康、建立社区中心、增加图书馆分馆等等,把社会改革、市民改良和市政规划、商业繁荣等整合起来。直到二战以后,1940年代的住房法案鼓励市民在郊区建设单门独院的房子,一批刚从二战及朝鲜战争回来的年轻的退伍军人得到资助也选择在郊区居住。同时还有公路法案使以车为主的宽马路、快速路、高速公路网迅速建设起来。波士顿的工业也随着战争订单的结束面临着转型升级。而郊区128号公路沿线在麻省理工教授们主导下新兴电子产业的崛起,吸引新开工企业以及波士顿城内现有的企业扩张或搬迁都选择到这里。
波士顿旧城却面临人口老龄化、底层化,建筑老化,交通拥堵日益严重。波士顿长期实行的对企业和富人的高税收政策也将新的投资挡在门外。旧城经济缺乏新生力量,一股强大的郊区化趋势让旧城面临更加严重的衰败和分裂的危险。城市呼唤留住知识阶层和年轻人,而长期固化的城市政治让市民对城市和城市领导者缺乏信心。
哈佛与波士顿/高校与城市
城市体现为一个社区和大家庭。高校绝不是象牙塔,大学没有围墙,它是一个教育社区,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隔离的封闭的单位、王国,是城市的资产,而且是增殖快的资产和驱动要素。三年前去波士顿,在哈佛校园周边塞特设计的住宅Peabody Terrace住过一段时间。宁静非常的坎布里奇镇,拥有大型超市和教堂集中的镇中心,以哈佛和MIT为主,学院和学校设施成组团分布。哈佛商学院与哈佛本部跨查尔斯河,靠近哈佛院子(Harvard Yard)有以地铁站为中心的哈佛广场,周边各种餐厅、酒吧、书店。沿主要道路马萨诸塞大道有很多商店,有地铁连通波士顿市中心和哈佛广场以及MIT。快速路和次干路沿查尔斯河连通市中心和周边地区,查尔斯河南岸还有波士顿大学以及东北大学等高校,分不清哪些是校产,哪些不是。
由原子弹、科技革命以及其它发明中专业团队所表现的关键作用上,美国人表现出对专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无限信任。高校以城市为样本,以城市为实验场,同时,高校也是居民,是产权人、投资者、使用人、纳税人。和哈佛一样,波士顿的其他众多大学如MIT、波士顿学院、波士顿大学、塔夫茨、东北大学等每个大学都可以参与城市事务,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雄厚顾问智囊团。
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州政府领导人很多是哈佛、波士顿学院和大学的毕业生。作为生在、成长在波士顿,并靠着个人的努力一步步走向政府书记官(City Clerk),并最终当上波士顿市长的波士顿人——约翰·B·海恩斯,他热爱波士顿,懂得波士顿作为一个城市社区和商贸中心的城市价值,对波士顿抱有唐吉诃德式的雄心和城市愿景。海恩斯在波士顿市中心Suffolk 法学院的夜校读过书,年轻时曾与一批外迁的中产知识阶层为邻。海恩斯善于利用主要学院和大学的支持,在他的带领下,波士顿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改造、城市何去何从的大讨论,引发了专业人员、建筑师、规划师的极大关注和思考。
也许正是这样的大背景,推动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设计研究生院的教授们开始反思他们对城市的作用和作用的方式。也是他们与城市领导者和市民的合作影响并主导了波士顿城市更新理念、方法和工具。1955年开始,在波士顿学院创设市民研讨会(Citizen Seminar),这是一个常设的研讨会。主办者想办法让更多不同的人参与对波士顿未来及面临问题的广泛讨论。来自各种背景的商人、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劳工领袖、政治人物、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等,在一个相互信任的、拥有共同良好愿望的氛围中相聚,讨论当时一些最紧迫的问题。
刘易斯.芒福德作为人本主义城市区域规划学者,时任麻省理工建筑学院Bemis教授,也是波士顿市民研讨会的活跃分子和常客。在一次研讨会上,他力主将目光从面向未来的摩天大楼、穿梭的高速公路转向城市的历史和城市中心。他认为波士顿在1890年代前后的发展停滞,看似落后,实则是旧城的幸运和财富,它让城市历史记忆和文脉得以较好的留存。何塞·路易·塞特在1942年出版《我们的城市能存活吗?》一书中,介绍了他关于城市和城市问题的概念以及解决办法,被尊为城市设计的“先贤”。他在1953年秋上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院长后,于1954年在哈佛开设了城市设计专业课程,从理论上“着手探寻解除当代城市‘可怕的顽疾’良方”,并广泛参与波士顿及纽约的城市更新项目。
回归城市思维
城市历来以人、资金、信息、服务的集聚和中枢为其功能,以多样性、复杂性为其特色,便利、可选择机会多。大规模工业化时代取而代之的是机器、规模、一体化、只注重效率、功能严格分区的城市美化。勒·柯布西埃的“光辉的城市”与当时国际现代建协的技术流就是其反映,以生产为本、以汽车为本、以技术为本代替以人为本,直至出现郊区化和逃离城市的趋势。
何塞·路易·塞特、刘易斯·芒福德、简·雅各布斯等提出的人本主义和对“大城市的生与死”的诘问,引导建筑师、规划师转向“小的是美的”。重新思考什么是城市和城市中心的问题:城市具有复杂性,注重场所感,有人的聚居,按照人的需求、感受、尺度以及社会关系来组织、建设和治理,注重邻里交往;城市中心是文化、学习和商业的中心;并回归“城市思维”的共识,即:
——回归城市中心、城市功能、城市品质,以人为本,满足人的需求,体现城市文化魅力。
何塞·路易·塞特:如果没有波士顿作为中心,新英格兰地区不可能如此繁荣;如果没有费城、芝加哥、旧金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成为文化、学习和商业中心,今日美国将不会成为这般伟大的国家。尽管伴随着过于拥挤的贫民窟和无情的投机买卖,我们同样也拥有了伟大的学习中心、博物馆、医疗中心、娱乐中心,所有这些都是城市文化的产物。
最美丽的城市必然是那些更和谐、更统一以及更具精神延续性的城市,置身其中,感受的不只是一座座孤立的纪念碑,而是在一个和谐而充满活力的环境中欣赏杰出建筑场所产生的愉悦。
槙文彦:创建城市形态和场所的复杂网络,便于人们相互愉快地交流。
简·雅各布斯:商店本身就是社交中心……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闲谈开始的……城市魅力体现在一些看似混乱不堪的区域……规划师必须更精明地设置商店的分区和布点,建筑师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设施以提升这些便利设施的社交功能……
——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相互隔离,不是简单的拼合,而具有有机体的复杂性,包括商业、居住、大学、剧院、博物馆、医院等功能。
何塞·路易·塞特:如果我们不想让中心城区沦为仅仅是一个商务中心或者交通中心,我们就必须了解人及其物质和精神诉求……将人作为考虑的核心,以尊重人的一切活动作为指导因素……
——城市是大家的,城市的规划与建设需要公共参与,发挥政府与相关人的作用。
亚历克斯·克里格:在规划设计阶段,任何发展规划或区域规划都需要超越专业性的合作才能完成,这些合作者包括直接相邻房地产的业主、周围的邻居、遴选的官员、公共机构、反对者、投资者、金融机构和管理者,统称为“利益相关方”。
何塞·路易·塞特:不能由城镇规划师一个人来决定人们的需要以及怎样能够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人体器官的复性及其物质和精神的愿望需得到他人的帮助……
反观我国的城市设计理念和实践,是否还处于哈佛会议之前的城市美化阶段?我们意识到了旧城更新、旧城需要活化、需要适当的小街区、密路网、开放围墙,但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城市,回归综合思维,回归人本。小街区密路网和开放街区只是手段,如何营造社区中心感?在互联网冲击实体零售商业时如何对待历史上延续的各层级商业中心/社区中心?在大规模拆迁改造后人口、商业店铺及学校、医院等城市设施如何再布局?城市经济、社会、文化脉络如何进行重构?单靠政府或规划师及市场等各单方面力量都将无能为力。
参考文献:
1.[美]亚历克斯·克里格、威廉·S·桑德斯编著,王伟强等译·城市设计,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
2.[美]Thomas H O'Connor. Building a new Boston: politics and urban renewal, 1950-1970,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







- 上一个:跟着共产党学管理之三:使命驱动的组织 2019-03-22
- 下一个:曹谦诗集(节选)2019-03-22
德成动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7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6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5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夸父逐日
- — 市政府国资委召开国资国企转型发展及“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