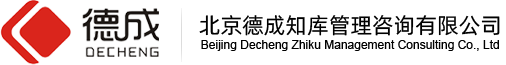本随笔是读《人工智能简史》一书的感受、感觉与感悟。我不是人工智能的专家,连初学者都不算,谈人工智能话题确实是知识储备不够、专业训练不够、智商不够。好在我大学学数学,学过布尔代数,也是学科“乌龟壳”的底层。这个布尔,就是被誉为“神经网络之父”和“人工智能教父”,并得2024年物理学诺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E. Hinton)的曾祖父。后学经济学,觉得人工智能不仅是个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及系统问题,更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制度设计是一个经济学话题,与制度经济学相关,似乎就有点发言权了。2024年物理学诺奖奖励的是人工智能,而经济学诺奖奖励的是制度经济学,我就把物理学诺奖与经济学诺奖一锅烩了。话题很大,我们聚焦在达特茅斯会议后,美国人为人工智能做了什么,中国人在人工智能做了什么,现在中国人应该做点什么。这里讲的“人”大约有二个约定:一是指大学的教师与研究人员,也涉及科技创业企业家;二是界定为理论、技术与产业的开创者、原创者、源创者、颠覆性与主要贡献者,那些追随者、模仿者、流创新者暂不算在其中。这个“人”也间接的涉及到政策的制定者。
一、美国人为人工智能做了什么?
我们从达特茅斯的会议开始。1956年暑假,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汉诺斯小镇的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的正式诞生,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的元年。当时的参会专家不多,大约10人。其中最大贡献者有: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达特茅斯学院数学助理教授(相当中国的副教授),会议的发起者之一,首次在会上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并在后来的工作中发明了Lisp语言并获得图灵奖。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哈佛大学数学与神经学初级研究员(Assistant Professor,不会高于中国大学的副教授),后来成为人工智能与认知学专家,图灵奖得主;并与麦卡锡共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AI LAB实验室,对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位副教授在一个小镇,发起全国性的、载于人类史册的学术会议,在中国估计难以想象。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其最有名的论文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奠定了现代信息论的基础,定义了信息、引入了信息熵(entropy)、提出了“比特”(bit)作为信息的单位,不仅对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密码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计算机科学家,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共同开发了逻辑理论家(Logic Theorist)程序,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蒙还因认知心理学、有限理性等获得经济学诺奖,等等。随后,我们就人工智能的几个主要领域,看看是谁在主导这些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我这里引用的是开创造与原创者,不包括追随者、模仿者、模仿创新者、流创新者及微创新者。为简单计,我把读《人工智能简史》中认为人工智能最内核的领域列出,然后简要列出主要贡献者。从达特茅斯会议以来,人工智能最内核的探索内容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技术、知识工程、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数据挖掘、计算机下棋等。正因这些领域的探索与推进,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其主要贡献的科学家,首推是艾伦·图灵(Alan Turing),是他给了计算机的“灵魂”,并在1950年提出了“学习机器”的概念,这是机器学习领域的早期思想之一。还有阿瑟·塞缪尔(Arthur Samuel),在1959年创造了“机器学习”这个术语。杰弗里·辛顿,以其在人工神经网络(ANNs)领域的工作而闻名,被誉为“深度学习之父”。他对反向传播算法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深度学习模型的性能 。当然还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这位革命性、领袖型的大神。作为一位杰出的语言学家,他开发了转换语法,对语言的计算建模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理论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结构的理解。在中国无人驾驶技术热上天的中国,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其实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塞巴斯蒂安·特隆(Sebastian Thrun)。达斯坦福大学教授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在概率图模型和机器学习方面做出了贡献,这些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语音识别。除辛顿外,纽约大学教授杨立坤(Yann LeCun,注意,起了一个中文名的美国人),他在卷积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对语言识别技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实,他在图像识别技术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教授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模型的研究方面做出贡献,也是蒙特利尔学习算法的提出者。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韩家炜(Jiawei Han),华裔美国人,他在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方面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或许给大众冲击力最大的是深蓝与AlphaGo。计算机下棋程序或更准确的说,“计算机棋类游戏程序”或者“计算机棋类博弈程序”几十年持续败给人类,终于在1997年被颠覆了。1997年,IBM的深蓝(Deep Blue,因为IBM称为“"Big Blue”)战胜了当时的国际象棋特级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这是“人定胜机”到“机定胜人”的关键节点;随后,2016年,AlphaGo战胜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2017年,AlphaZero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连续60局无一败绩。在人工智能产业方面。当然首推马斯克(Elon Musk),他不仅创办的特斯拉和SpaceX,也是OpenAI和Neuralink的创始人;他在自动驾驶、人工智能芯片、Dojo超级计算机以及Optimus机器人等多个AI创新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其次,有吴恩达(华裔美国人,出身在英国),谷歌大脑(Google Brain)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在线教育平台Coursera的联合创始人。他在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教育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AI技术的普及和教育。杰里米·霍华德(Jeremy Howard),Fast.ai的创始人。fast.ai在产业中的影响力非常显著,它的课程已经达到了600万播放量。黄仁勋,英伟达(Nvidia)CEO、总裁及联合创始人,其公司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微处理器的主导制造商,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的普及,对Nvidia芯片的需求呈现爆发性增长。
二、中国人为人工智能做了什么?
似乎整个人工智能史都是老外的历史,特别是老美的历史。中国人鲜见其名,有名也是在美国取得的成就的华裔美国人,比如逻辑学家王浩。在机器证明领域,华裔美国人的逻辑学家王浩,在1958年夏天在一台IBM-704机上,只用9分钟就证明了罗素与其老师怀特海著的《数学原理》一阶逻辑的全部理论,要知道《数学原理》有三卷,近2000页;可以说没有《数学原理》,就奠定不了20世纪数理逻辑发展的基础。《数学原理》不仅在数学和逻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其他诸多学科也必然产生至深、至远、至广的影响。我们知道,在学科之间存在一种“乌龟壳”比喻:最底层的“乌龟壳”是数理逻辑,在其上的“乌龟壳”是数学,是底层数理逻辑为数学提供基础;随上是物理学的“乌龟壳”,是数学为物理学提供基础;再是物理学为化学提供基础,化学为生物学提供基础,生物学为心理学提供基础;最后,心理学为哲学提供基础。这样的“乌龟壳”层次结构比喻,反映了从最基本的逻辑和数学原理出发,逐渐构建起对世界更复杂现象的理解。遗憾的是王浩是华裔美国人,是美国人,华裔只是证明了华裔这个种群的智商没有问题。比如,还有以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当然,难能一见的中国学者名字要算吴文俊先生了。吴文俊先生早年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年近六十,开始学习Basic,后学习FORTRAN语言,借助计算机语言他开拓了几何证明的新路径。实际上,我们到处看到的是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及斯坦福大学的名字,鲜见清北及其他中国大学的名字。吴恩达也为人工智能做出大的贡献,可惜也是华裔美国人,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副教授。为什么达特茅斯会议后,看不到中国大学在做什么呢?我们做一个简要且不深入的概述。1956年,中国提出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将计算机技术列为重点发展的科学技术之一。1957年,大学在反右。(因发表原因,此处省略……)1958年,大学在放卫星。一是大学激增。全国新增高校数量达到了562所,许多是“人民公社大学”;二是大规模扩招。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约50%,招生数增长了约150%;三是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断正常教学计划;三是“土法上马”“超英赶美”。夸大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造的飞机不能升天、造的汽车不能动。虽然如此,1958年,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机”研制成功。1959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由于粮食短缺和经济困难,学校不得不减少课程数量,学生们不得不忍受饥饿,不得不参与劳动,支持农业生产和经济恢复,科学研究没有活下来重要。1965年,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109丙机”。1966-1976,全国所有大学停止招生。有成就的大学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游街、架飞机批斗;年轻有希望学者,被批为“白专苗子”,下放农场改造,等等;其中1968至1966三届2000万高中生与初中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学瘫痪、遑论科学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教育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发展。一是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中国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全国高考,570万青年参加了高考;二是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强调“不抓教育不行”,等等。中国大学老师真正可以专心研究了,可惜的是,那时,都不知道世界科技发展到哪里了。21世纪,中国学者开始在人工智能方面出现不少人才,也做成不少成果。比如,李飞飞,她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视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它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还有不少中国学者也做出一些贡献,但他们受的教育主要是欧美,还不能说是革命性、颠覆性、源创新的。乔晓春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一书中指出,本书揭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不科学”“非科学”乃至“伪科学”的现状。复旦大学某教授连续三届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或许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一面镜子,折射了中国科学研究的现状。此外,中国大学教师,忙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大学老师在做什么,在做被行政指挥棒指挥的周期性评估,造假性评估,在为考评科研分发表难有原创性的论文与成果而焦虑。
三、现在中国人应该做的什么?
2024年经济学诺奖表彰三位经济学家在“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方面的贡献。他们的主要观点包括:一是他们通过研究殖民历史,发现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而掠夺性制度,导致了长期的贫困;二是他们指出,在工业革命前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我理解的是三点:一是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孵化器。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就像孵化器为新生命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一样;二是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的助推器。因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产权保护、激励创新和创业,从而加速技术的应用和扩散;三是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可能难以实现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制度决定了资源的配置方式、激励机制和行为规范,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中美大学在人工智能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其一,科学研究的基本条件是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是对自由的探索。在美国,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的底色;而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创办企业只是这个国家的特色。制度对于美国大学的教师、研究人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是空气般的存在。在某些国家,制度可能就是自来水、吸氧器。掌控自来水龙头开关的人、控制吸氧器的人,关了开关或拔了吸氧器,你在大学就活不下去。在某些国家,产权都得不到保护,何言知识产权保护。其二,让大学与政府保持合适的距离。中美大学最大的区别可以这样说:美国大学离政府最远,一定是独立于政府的大学;而中国大学离政府最近,或许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当前大学的衙门化是愈演愈烈,大学“一把手”校长来自政府官员的越来越多,来自学者型的越来越少。要促进大学的理论创新,只有从大学的顶层去设计。调整距离、去行政化、去衙门化、去官僚化,增强学术自主性;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减少行政部门对大学行政化评估,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与精力专注于教学、科研与科技转化。唯有如此,大学教师与研究人员的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才可能是一个可以言及的话题。其三,要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构建大学的多边治理结构,实施合理的“学术权、行政权、学生权”的三权分立/设。特别是大学的学术权力,必须得到保护与捍卫。包括课程设置、学术标准、教学方法、研究政策以及学位要求等,行政不得染指。要调整当前学术委员会的组成,限制行政人员参与学术委员会,确保学术事务的决策独立于行政权力,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教育质量。其四,让科学研究回归科学。要强调“无用之学”,强调“为研究而研究”的学术氛围,而中国的传统的“研以致用”,从《周脾算经》到《九章算术》都是如此。其实,强调“研以致用”可以,但强调基础理论研究也不为过。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产业创新与产品创新。可以说,牛顿力学、热力学、电磁理论和量子力学这些当时的“无用之学”,现在则是现代人类社会幸福的四个基石。因为有了牛顿力学,我们才有汽车、摩天大楼、跨海大桥;因为有了热力学,我们才有发电站、核电厂,人类不再在黑暗中生存,不再在炎热与酷寒中度日;因为有了电磁理论、量子力学、信息论、材料科学,我们有了须臾不可离手的手机,才不会“家书抵万金”;因为有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理论、认知科学,我们就可以通过ChatGPT聊天了。其五,从改变中学传承下来的应试教育开始。当下,“以学生为中心”成为教育行政部门考核大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质疑的理念与教学模式。从我在大学40多年的教学经验看,大学低年级学生,刚进大学,带着应试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的学习范式与教学“范式”,突然要求他们进入“以自己为中心”的学习与教学“范式”,这有点勉为其难,教学效果极差。大学与中学最大的不同是,中学的课堂是确定性的课堂,大学的课堂是不确定的课堂,这样师生之间知识、思想才能碰撞出火花,才能有创新的思想,看看人工智能的师生思想的碰撞与科学研究的传承及创新,可见大学与中学,课堂教学是不同的。此外,既使是进入大学一年后,要他们自学“线性代数”“抽象代数”“拓扑几何”“集合论”“高等微观经济学”“动态规划”“数理经济学”是否可行,结果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当下,大学首先是要补中学缺失的逻辑思维训练环节。维特根斯坦说过:“逻辑似乎处在一切科学的底部——因为逻辑的研究是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没有逻辑思维,哪有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以逻辑思维为基础,并超出逻辑思维的。遗憾的是,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学生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反出现了倒退。批判性思维的倒退,自然是创新思维窒息,科学理论创新则不可言及。其六,为科学研究营造好的“营研环境”。不要每年为老师设置科研考核,设置科研分,很多研究不是一年能出来的。老师为教学工作量、为科研分焦虑,没有时间读专著与原著,心放不下来,脑就不能启动,就不能激发思想的火花与灵感,谈何原创。这我们确确实实可以学习欧美大学的一些经验。我们知道,费马大定理是数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未解决问题,它由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皮埃尔·德·费马提出。这个定理断言,对于任何大于2的自然数n,方程a^n+b^n=c^n没有正整数解。这个定理在数学界引起了长达数百年的探索。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的怀尔斯,9年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论文,学校也不考核,最后解决百年人类未解决的世界难题。再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尽管因病无法正常工作,普林斯顿大学仍然非常支持他,在他能够工作的时候,经常为他找到工作机会,他的病情并没有阻止他在此期间做出一些非常原创和高技能的工作。纳什被称为Fine Hall“费恩楼”的“幽灵”,因为他会在任何时候在学院的大厅里徘徊,在黑板上写下复杂而神秘的公式;Fine Hall 为纳什提供借书卡与座位,这就是普林斯顿。最后,学习美国企业家资助“无用之学”的大学与科学研究。约翰·洛克菲勒创办芝加哥大学,利兰·斯坦福夫妇创办斯坦福大学,安德鲁·卡内基创办卡内基梅隆大学,埃兹拉·康奈尔与其他企业家共同创办了康奈尔大学,这与中国企业家创办大学以营利有天壤之别。此外,美国不少企业家不资助“有用之学”,而是资助“无用之学”、资助“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最典型是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向哈佛大学捐赠了5.19亿美元,用于启动和运营哈佛大学自然和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领域将涵盖学习和记忆、大脑功能、感知和感觉以及元可塑性,提高我们对人体和世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