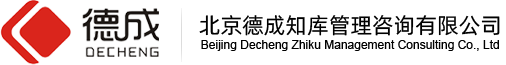当前位置:走进德成 > 专家观点
我的老师 杨卫东 北京德成智库
发布日期:2019-09-16 来源: 作者: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加入收藏


今年是我的导师萧致治先生九十寿辰的日子,师兄弟们合议为萧老师筹办一个庆典活动。
由此就想写点文字,记述我与老师的情缘,虽然当下文债累累,心中却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由萧老师联想起我的许多老师,他们在我人生道路上像一座座烛台,一把把火炬,启迪和指引着我前行。
(一)
王老师肯定不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在我幼小心灵中能记起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她。她的形象随着时间的拉长在记忆中逐渐模糊了:中等身材,白白的皮肤,圆圆的脸颊,慈眉善目……在我的脑海中她常常和我母亲年轻的样子重合。
据说,自从父母结婚开始,我家就一直有八九口人,当然人口结构总在调整:老人不断地离开,亲戚不断地独立,新人不断地诞生。虽然父母是双职工,全家的生活水平却一直处在贫困线的边缘。
我已经忘了在我上学前,家里是谁在做饭,只知道上学后有一段时间做饭的重任落到了我的身上。
一天, 王老师来到我的身边亲切地问道:
“杨明俊(文革初期被大哥改名杨卫东),听说你在家里做饭?”
“是的。”
“我考考你,白菜怎么做?”
“首先把锅烧热”其实,我只是负责做饭,但我依稀知道炒菜的基本程序:“然后把猪油烧开,然后把白菜放进去,快熟了的时候再放盐。”
王老师笑眯眯的看着我,竖起拇指夸奖道:“很好!我们的小炊事员!”这个表扬让我高兴了好一段日子。
不久,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票五分钱一张,但父亲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五分钱的申请:“看什么电影?!好好地用功学习!”
王老师不希望我一个人落下,于是她在班上作了一个小的动员:“同学们,在你们中间有一位同学家里困难,没有钱买电影票,谁愿意学雷锋把自己的电影票捐献出来帮助这位同学?”
“我愿意!”全班的同学都举起了小手。
最后,王老师没有让学生捐票,而是让学生们高举着票簇拥着我,帮我混进了电影院。这事现在回想起来,王老师的做法或许是有瑕疵的,但她的爱心,她的慈悲感染了我一辈子。
大约是上五年级的时候,瞿义华老师作了我们班的班主任,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头发花白、经验丰富的老师,年龄估计比我父亲还要大。
这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在全国铺开了。我们的班按照军事编制的名称变成“排”,每个年级被称为“连”。在此之前,我在班上一直默默无闻,连小组长都没有当过,在我的记忆中,曾被一位音乐老师即兴任命过一个职务——“抬琴组长”,那是我曾经津津乐道的唯一职务。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引起了瞿老师的注意,我突然被他提拔为副排长,不久又任命为副连长!或许他想证明任何人只要给他相应的环境和条件,都可以由小丑鸭变成白天鹅?
我既兴奋又紧张,更多的是茫然不知所措。瞿老师不断地鼓励我,教我怎么当干部。一次,我被安排大会发言,开会前瞿老师专门对我进行培训:“大会发言不要两眼盯着发言稿,发言不是唸稿子,眼睛要更多地关注会场,要对着大家讲话。”
一颗小小的心灵似乎被启迪、被唤醒,从此,我开始用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带头参加各种活动,以身作则,为人表率……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小升初不再需要考试,而是以就近划分的原则,由行政命令安排,我们大兴路小学毕业生全部分到了新建不久的人民中学。
我初中的班主任老师叫李全英,一位武汉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文革结束后又调回武汉大学数学系。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是一位既漂亮又温柔,既认真又活力四射的大姐或阿姨。她家住武大,回家时走大董家巷要从我家门口过,所以经常来我家坐坐,开展家访,与我父母也结下了较深的友谊。她经常给我交办一些任务,也经常纠正我的缺点,记得有一次,她批评了我,但我不服气,为了表示自己的耿直与倔强,居然跟她拍了桌子,但这件事好像她完全没有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爱护我。记得有一次,学校评寒衣补助,我家一直处于贫困线的边缘,我虽然从未穿过棉衣,却一直不申请,大家投票公议,给了我补助,我坚决拒绝,她耐心的跟我做工作,让我体会大家的心意,也体谅家里困境,终于在李老师的说服下我穿上了人生第一件新棉袄,一件军绿色,被线行成凸起的竖条条粗布棉衣。
我们的初中毕业有三大去向,一是下农村,二是到服务行业做“八大员”,三是升高中,我属于40%升高中的一类。进高中不久,我莫名其妙的作为学生干部从李全英老师班上调到了熊光祚老师班上任排长。熊老师是俄语专业毕业的,文革后中苏关系恶化,停止了俄语教学,熊老师转而教授英语。
熊老师应该比我父亲略小几岁,据说是得过骨结核的原因,他的左手不能伸直,总是像周总理一样弯曲在胸前。他既严厉又随和,我们许多同学都经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见识、有胆略、勤思考、敢行动。绝大多数同学都被他的才华所折服,在毕业许多年以后仍和他有较多的交往。我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也是受他教益最多的弟子。在他那里,我学会了独立思考,学会了怀疑的思维,减少了对权威的盲从与迷信;在他那里,我开始辨别新生事物,亲近标新立异,乐于创造创新。在他的带领下,我多次参加了教育革命和上山下乡的实践,这些内容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或许是不值得称许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我个体而言却是获益良多的。
(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有幸成为武汉大学历史系77级学生。大学没有班主任制度,学生与老师的接触往往只限于课堂中,但仍有一批老师让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唐长孺先生、吴于廑先生是名震史学界的泰斗,唐先生是历史系的主任,吴先生是武大的副校长,是他们创造了武大历史系辉煌的“唐吴时代”;李则鸣老师是教中国古代史的,他的形象我已经有一点模糊了,但他给我们作的自我介绍仍记忆犹新:“同学们,我叫李则鸣,不平则鸣!”;教中国古代史的老师中陈国灿、黄惠贤、卢开万三位老师的课各具特色,陈老师深入浅出、黄老师逻辑严谨、卢老师激情四射;中国近代史老师中,李天松老师曾与我们交往最密切,他交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三峡的课题,并利用暑假的时间带领我们几个同学朔江而上对三峡进行了调查采访,最后大家合写了一本《三峡纵横谈》由武大出版社出版。对此,我一直对李老师心存感激;王承仁老师性情耿直、上课认真,在给我们讲太平天国运动时,对农民起义的感情溢于言表;柏盛湘老师是历史系副主任,年轻力壮,充满活力,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打篮球,与大家相处甚好;吴剑杰老师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我本科的毕业论文是他指导的,当时隐约知道他文革前研究生毕业,是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调回武大的,他言语不多,但思想敏锐,有一种学者的风范。
在我的记忆中,读大学本科时就曾见过萧致治老师,但那时只是远眺,并没有听过他的课。或许因为那时他正带研究生没有精力开课,或许是我错过机会选他的课。我原本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不擅长交往,更不爱打探,所以对萧老师是陌生的,真正近距离或零距离接触萧老师,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的。
选择读研究生其实是一项临时的决定,1978年初进武大时我已23岁多,四年本科之后,将年近28,原本没有继续深造的打算。一次同学私下议论毕业分配消息,谁谁有关系,谁谁找了谁,说得活龙活现,好像大部分同学去向已定,剩下的估计没有好的去向。怎么办?我本一草根,没有任何门路,只有横下一条心,自己救自己——考研。
本科期间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一定兴趣,曾写过一篇读书笔记《一条循序渐进的改良路线——论张之洞的“劝学篇”》受到周谷城先生的好评。八一级研究生招生目录正好有姚薇元先生开的鸦片战争史专业科目,于是我决定一搏。在此之前,姚薇元先生开过鸦片战争的专题课,我曾去听过几节,因为与其它课有冲突,加之姚先生的口音很重,许多话听不懂,故而没有坚持听下去。决定报考研究生后,我鼓起勇气去薇元老师家拜访,他问:我开的专题课你听了吗?我对你怎么没有印象?我十分尴尬,不得不据实回答。姚先生很宽厚地一笑:好好准备去吧。
在忐忑中收到录取通知后,我对姚先生的宽厚大度怀有深深的敬意,后来听说考前我国一个著名的老作家曾向他推荐过研究生人选,但他不徇私情,坚持量分录用,更让我对姚先生品格崇敬有加。
由于当时研究生的数量很少,我们享受的教育几乎是一对一式的培养模式,姚先生与萧老师两位老师带我和李少军两个学生。除副课外,主课都是在姚先生家里上的。一杯茶,几盘干点,是一种聊天式、讨论式的上课。这既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也是一种学术思辨的训练,每一次的上课如同聚会,都是由萧老师事先安排好,大致的程序是我们先汇报近期学习情况,读了什么书,有一些什么见解和疑惑,然后一起讨论或由两位老师进行点评。通过这样的学习,我们不仅得到了学术训练,把握了前沿的学术动态与思想,而且也了解到一些历史学界的轶闻趣事和学术脉络。
我们踏入研究生的门槛时,姚老师已达77岁的高龄,是史学界资深的教授,他上世纪30年代入清华大学历史门,师从陈寅恪大师,研究生毕业不久,即被多家大学相继聘为教授。
在研究生期间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陪同姚先生、萧老师到外地考察,我们从福州、泉州到广州,还专门上了海军的登陆艇去查勘了虎门要塞、横档,然后萧老师返校,我们继续陪姚先生到杭州、镇江、南京、上海。到上海后,姚老师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家中宴请了我们。一路上姚先生通过实地考察让我们对鸦片战争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我曾认真学习了姚先生的《鸦片战争史实考》、《再论<道光洋艘征抚记>的祖本与作者》,对他的文笔和考据的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姚先生曾在他的“茶点课堂”聊天时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表达没有文采,就不能传播到很远。”这句闲谈深深烙在我心里,潜移默化地成为我写论文或文章的一种原则和习惯。
(三)
研究生期间,我们与萧致治老师的联系更频繁,虽然名义上他是导师助理,由于姚先生年事已高,对我们的学业指导实际上主要是由他负责。萧老师与我父亲同庚,身材欣长,充满活力,语速快、步伐快、行动快,让人常常联想起“雷厉风行”这个词。
萧老师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长期在武汉大学执教,专攻中国近代史,尤其在鸦片战争和辛亥革命两大领域成绩卓著。他思想开明,为人谦和,待学生如兄弟,从不以命令的方式给我们布置作业,从不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即使不成熟、不合潮流的观点,也让我们充分表达。
我曾梳理过研究生三年的学习情况,萧老师指导我完成了如下工作:一是为了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关于林则徐研究的学术会议,萧老师让我准备一篇关于林则徐研究述评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前提是必须尽可能地读完截止当年的所有关于林则徐研究的书籍和文章,不仅要“述”,重点在“评”,由于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通过这样的研究,使我较快地了解了鸦片战争史研究的相关情况;二是1982年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牟安世先生出版了《鸦片战争》一书,这是当时一部篇幅最大的关于鸦片战争研究专著,萧老师让少军和我对该书写一个书评。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方法,它不仅要求我们反复读牟先生的书,还要比较研究该书与以前关于鸦片战争文章、书籍的异同,研究牟先生的观点与不足,这是对史实、史论、史识的全面训练。三是萧老师要求我和少军各翻译英文与日文的历史专著。我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翻译了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萧老师原本准备推荐出版,遇上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译著从严。我离开学校后没有精力再去关心此事,1988年该书由王小荷翻译出版。这项翻译不仅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更重要的是,受该书启发,成就了我硕士论文的选题。四是为了收集撰写新的鸦片战争史专著的史料,萧老师让我们在北京故宫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泡了一个多月,抄写了许多道光年间的奏折、书信和相关资料,这不仅提高了我查找历史档案的技能,也培养了我读原始资料、第一手史料的兴趣。五是给我布置了一篇大作业,让我系统收集整理鸦片战争前中西的交往历史资料。这些资料散落在过往的历史书籍、文章、书信、笔记之中,不整理出来,就不能理清中西交往的脉络,就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历史起源,这是一个较大的史料整理、史料考证、史料勘误的工程,在萧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我按照年代顺序,并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拿出了一个《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的初稿,由于时间太紧,加之硕士论文期限在即,以至初稿十分粗糙。承蒙萧老师不弃,对初稿耐心删改、修正,并给予了大量充实,许多章节几近重写。该书1986年出版,2005年再版时,萧老师根据新发现的史料,又新增了8万字的内容。这一次的作业对我史学的锻炼是尤为珍贵的。六是我的硕士论文,这是每一个合格的研究生必须完成的任务,由于前期的大量研究,为硕士论文打下较好的基础,我选择了一个鸦片战争中司空见惯却无人研究的课题:广东的团练。该课题在萧老师的指导下,几经修改、反复打磨,对我论文的写作有很大的提高。后来该文的部分观点,整理修改后经萧老师推荐发表,新华文摘给予了摘要介绍。七是《鸦片战争史》部分章节的撰写,当然,这个写作在研究生时只作了一些初步工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离开学校后做的。总之,三年间仅我一人写过的文字大约近百万。除我之外,还有少军兄,他比我更刻苦,所写文字可能更多,而这些都需要经由萧老师审阅和修改,其工作之繁重与辛苦,由此可见一斑。
萧老师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我们学生身上,我们的每一个习作,他都会认真的审阅批改,并动用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源,将我们的习作推荐发表。对于我们习作中值得推敲处,他总是以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讨论,让我们明白道理后自己修改。在新著《鸦片战争史》的署名上,包括前后排序他都很细心,专门和我商量,本来作为主编,排序是他的权力,但他从不专断。
在和萧老师的接触中,我深知萧老师是比较喜欢我的,虽然,他从未当面表扬过我。姚先生和萧老师都曾明确地希望我能继承他们的事业,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作贡献。我曾也有此意。但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激起了我投身改革的热情,由于毕业临近时,姚先生正处病危之时,我不敢流露我的想法,直到姚先生逝世,我留校后才把这个想法向萧老师报告。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的情景,面对我的请求,萧老师十分意外,脸上流露出万分惋惜且夹带着淡淡的苦涩,为了成全我的理想和抱负,他忍痛同意了我的请求。那种无私与深情的眼神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四)
1985年4月在刘道玉校长的关心与支持下,我在学校入职两个月后重新调整分配,分到了武汉市委研究室。从此离开了武大,与萧老师的联系也少了许多。但每年春节我一定会去给萧老师拜年,听听他的教诲,分享他学术的喜悦。
几乎每年春节拜年,萧老师都是在家中客厅兼书房的地方接待我,我发现他的书桌上总是堆着正在看或正在写的书。每次和我聊的话题也都离不开正在写的书。或是《鸦片战争史》,或是《黄兴评传》,或是《黎元洪新传》,间或是赶写某篇论文,完全看不出他退休与未退休之间有什么区别,这种对学术的酷爱与追求,这种笔耕不辍的境界每每都让我感动。
今年春节拜年,我想萧老师已经90高寿了,应该歇歇了吧?我试着问他:“您现在手上还有东西要写吗?”
“有啊,湖南出版社已经催了我几次了,一本关于黄兴的读物,今年上半年要交稿。”他告诉我,近几年张师母身体不好,很多事情需要他照料,现在他每天早上四点多钟起床,做完各种家务,9点以后便开始写作。
“您到现在为止一共写了多少东西,作过统计吗?”
“前不久,我回忆了一下,到现在,已经出版著作包括部分合编在内,一共有25种;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252篇。我是1992年退休的,退休20几年是我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25部著作,其中15部是退休后出版的,252篇文章中,退休后发表的有170篇。”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退休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性文章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强,退休后出版的著作占总数的60%!更重要的是学术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据统计,退休后发表的学术文章中《求是》有1篇,人民日报有4篇,光明日报有7篇,历史研究有2篇,近代史研究有1篇,新华文摘有2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选载有14篇。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奖项绝大部分都是在退休以后取得的,如中央“五个一工程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并两次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以及省部级奖多项。
- 上一个:泌阳女娲补天,伏羲演八卦创世神话与石符遗迹解读2019-09-16
- 下一个:观音寺的朝霞和晚霞2019-09-16
德成动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7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6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5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夸父逐日
- — 市政府国资委召开国资国企转型发展及“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