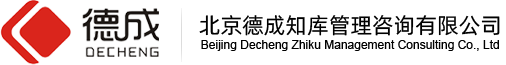当前位置:走进德成 > 北京德成经济研究院
从秦二世而亡看血缘传承的有效与有限 (甘德安 北京德成)

从秦二世而亡看血缘传承的有效与有限
秦朝二世而亡与刘邦白马而盟
秦朝,中华民族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如同诗人李白所言: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在我们中学历史课本中常出现秦王朝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贡献: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经典判断则是:天下苦秦久矣,以及焚书坑儒,这些都写进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了。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之后,自以为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于是把秦王改号为“皇帝”,并昭告天下:朕就是始皇帝,後世依次記数,由二世、三世直到万世,如此无穷无尽地传承下去。没想到二世而亡。二世而亡的不仅是家族王朝,家族企业二世而亡的案例也层出不穷。一个是当前的山西海鑫钢铁破产事件,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横空出世并二世而亡的王安电脑公司。家族企业与家族王朝在血缘传承上本质是一致的。我们从血缘视角把它们作为一个问题讨论。
秦王朝二世而亡反思很多。大多数学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始皇帝废封建、建郡县、自毁长城;其实,始皇帝废封建、建郡县的路径选择也是有多重考虑的。始皇帝废封建、建郡县的路径选择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选择;也是接受了宰相李斯的“后属疏远”建议,即亲属关系会随世代而疏,作为封建制基础的血缘内聚力则会随之解体而做的战略决策,这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万万没有想到,没有启用血缘传承制度导致二世而亡。没有选择血缘传承的不仅有秦王朝,还有西楚霸王项羽分封异姓十八王,五载而亡。
于是,刘邦总结历史教训,刑白马盟:“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一是血缘传递几代之后,血缘的凝聚力下降;二是皇权血缘传承也会产生分支对主干的反叛。两千年专制史可以看出一个规律:不实施血缘制度二世而亡;实施血缘制度也后世必反。血缘制度的主干在不断封王,而非主干则坐大造反。刘邦大封刘姓王而导致七王之乱,晋武王分封子弟导致八王之乱;明有靖难之师。管东贵教授指出,中国血缘制度第一阶段在周代是单血缘支配的封建社会;第二阶段则形成了始于秦、成于汉、终于辛亥革命的血缘郡县双轨制。
从血缘到地域:东西方文明路径的分叉
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家庭都是共同的文化基础与发展的基础,许烺光先生用初始集团表示家庭。许烺光先生指出,东西方的“初始集团”都是一样的;“在各种人类集团中,家庭对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无处不在的。”然而,中国人与西方人在“二次集团”的选择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人类的社会需求首先要在“初始集团”中得到满足,当“初始集团”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时,人们便要在“二次集团”中寻求满足。
中国人为什么特别重视血缘,主要是在“亚细亚的古代”这一黄河文明的条件下,中国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而将其中的血缘因素世俗化,从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强化了血缘伦理。而希腊人在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其中的自然因素神秘化,从而导致了西方式的宗教文化。
许倬云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一书中指出:希腊人群结合原则是地缘的、合约的,不是亲缘的。而古代中国移民是填空隙,不是长程移民,这就形成血缘为主、地缘为辅的同姓特性。例如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族群号称兄弟关系,一个生在河这边,一个生在河那边,这当然是后来的融合。周代以来选择以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特征就是建立在以血缘为主、地缘为辅,在血缘与地缘之间建立起来的社会与国家。

为什么古代的希腊人与古代的中国人会在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下做了不同的文明路径的选择?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去考察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
先看中国地图。虽然中国版图有大小之变化,但地处东亚的自然环境,基本特征未变,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在地球上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上。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有戈壁沙漠,北有寒冷多风的荒原或冻土,南方是多山地带,崇山峻岭,猛兽出没,多乌烟瘴气。可以说,中国人是在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生长环境生长,导致中国人的封闭性。

再看欧洲地图。其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处在地中海、爱琴海及爱奥尼亚海的包围之中。这种以远洋运输为生存方式的环境,必然导致不同中国人的路径选择。作为希腊城邦制度的准备阶段,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有了铁器,二是大量移民。铁制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私有制社会创造条件。而大规模的海上移民导致怎样的后果,用汤因比的推测是:“跨海移民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跨海移民的另一个显着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

新的生存方式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出现,私有财产的出现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了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而跨海移民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血缘纽带的断裂。在这个行为方式下,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的财产和能力,而不取决于他的家族和血统。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
这一切看似并无关系的偶然创造,实质上都是必然的、有条件的、彼此密切相关的,是希腊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所做出的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性选择。这便是我们西方从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的图腾崇拜到人类与自然的神话的神灵崇拜再到自然神话的加工的宗教精神的文明路径。正如《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所指出的:“智人优于动物之处,在于智人可以构建共同的“想象”/谎言/神话,而共同神话使得人类的族群认同得以突破150个的数量上限,能够达成更大范围的合作。”没有宗教文明的想象,就没有现代工业革命。

中国历史的核心观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土地属于皇权而非私有,虽然土地皇权所有否定私有,但对王侯领主们留了一个对土地有一个控制和使用的世袭权力。也就是,一方面根据血缘和亲疏关系,将一部分土地分给自己的子弟;另一方面则承认地方宗族势力的合法地位。这就在中国长期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血缘性、地域性很强的“宗法”管理体制。这便是华夏民族从自然与血缘的神秘统一的图腾崇拜开始,转向以血缘人化祖先崇拜的路径上来,最后通过对血缘关系的提炼而形成的儒家伦理精神的文明路径。
.jpg)

学习日本经验:血缘传承与契约精神的融合
日本虽然继承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大处看,有着种种近似之处,深入分析下去在血缘问题上却存在巨大差异。日本的家更多是地缘意义上的家,而中国的家更多是血缘意义的家。日本虽受儒家文化影响,但其地缘意识重于血缘意识。这种区别是通过养子制度所体现的。中国人的家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而日本人的家以家业为中心,家业包含了男方女方的血系和家产等。财产传承是不可动摇的,而血统则是可超越的。
中国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说的“后”是指男性孩子,并不包括女孩。而日本人不仅重视男方血缘延续,但并不排斥女方的血缘延续。这就是养子制度中的婿养子制度。所谓“婿养子”就是“收养子且让其与女儿结婚”。当然,中国也有上门女婿,它跟日本“婿养子”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上门女婿保持本姓,只是让孩子跟岳父姓,而日本的“婿养子”一律改为妻家姓。松下公司的平田正治更名为松下正治正是婿养子制度的体现。
在日本社会,男性的生存之道就是三子之道:当长子、当浪子、最后回归当养子。养子制度,也就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契约制度。据统计,14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旧民法就规定,家业和家名必须要嫡出长子继承。由此导致次子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处于不被重视、不受欢迎的地位。如此境遇,次子们只能选择离家外出谋生。对于财产,次子也无法分到家中财产,即使分到少量财产,也难自立门户,这只能导致次子选择到别家充当养子,还可以得到颇为可观的财产和出人头地的机会。这种制度的设计与文化的习成,使得日本四分之一的男子成为养子,再加上四分之一的养父,即全部男子的二分之一被卷入关于养子的契约关系中,即在日本每两个男人中有一个具有养子的契约关系。在日本众多的首相中,寺内正毅、高桥是清、加藤高明、滨口雄幸、吉田茂、岸信介都是养子出身。日本之所以拥有5万家百年家族企业,关键的是超血缘的养子传承制度。这也是中日两国文化最深层、最本质的差异,也是自唐代以来日本全盘学习中国,却越走越远的根源所在。
日本这种不拘泥于亲生子、超血缘的养子继承模式是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的一种模式。一方面可以把企业传承给相对优秀的人才,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另一方面又兼顾了传统东方文化重视家族薪火相传的文化。
企业发展越大、历时越长、血缘内聚力则越小,这是家族的血缘制度与企业的经济组织基业长青制度设计的一对矛盾。血缘传承不仅涉及到子孙不肖、缺乏能力、富不过三代的人性问题,更有传承百年后的堂兄弟妹及堂兄弟妹的堂兄弟妹的问题。或许,企业在创办之初时血缘制度是有效的组织,企业发展大时则是阻碍企业发展的瓶颈。企业传承不借助血缘则企业不安全,依赖血缘则做大、最强、做久则血缘则是瓶颈与危害。所以,家族企业传承应该在血缘与职业经理人之间找平衡。血缘团队中有能人则可以子承父业,没有则请职业经理人。此外,请职业经理人的进度也与中国社会诚信制度建立同步才好。
日本超血缘的养子制度是值得中国家族企业学习的。著名法学史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一切进步性社会的运动,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即从人身依附或身份统治关系让位给日益增长的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容和实质。
(本文作者系北京德成经济研究研究院院长甘德安教授)
- 上一个:跟着共产党学管理之三:使命驱动的组织 2019-02-19
- 下一个:高新区的核心是高技术(甘德安 北京德成)2019-02-19
德成动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7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6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5 往事并不...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1.3 清末官督商办之...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2 从重复博弈...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
- — 夸父逐日
- — 市政府国资委召开国资国企转型发展及“十...
- — 第一篇 历史博弈 1.1 熵与血缘大...